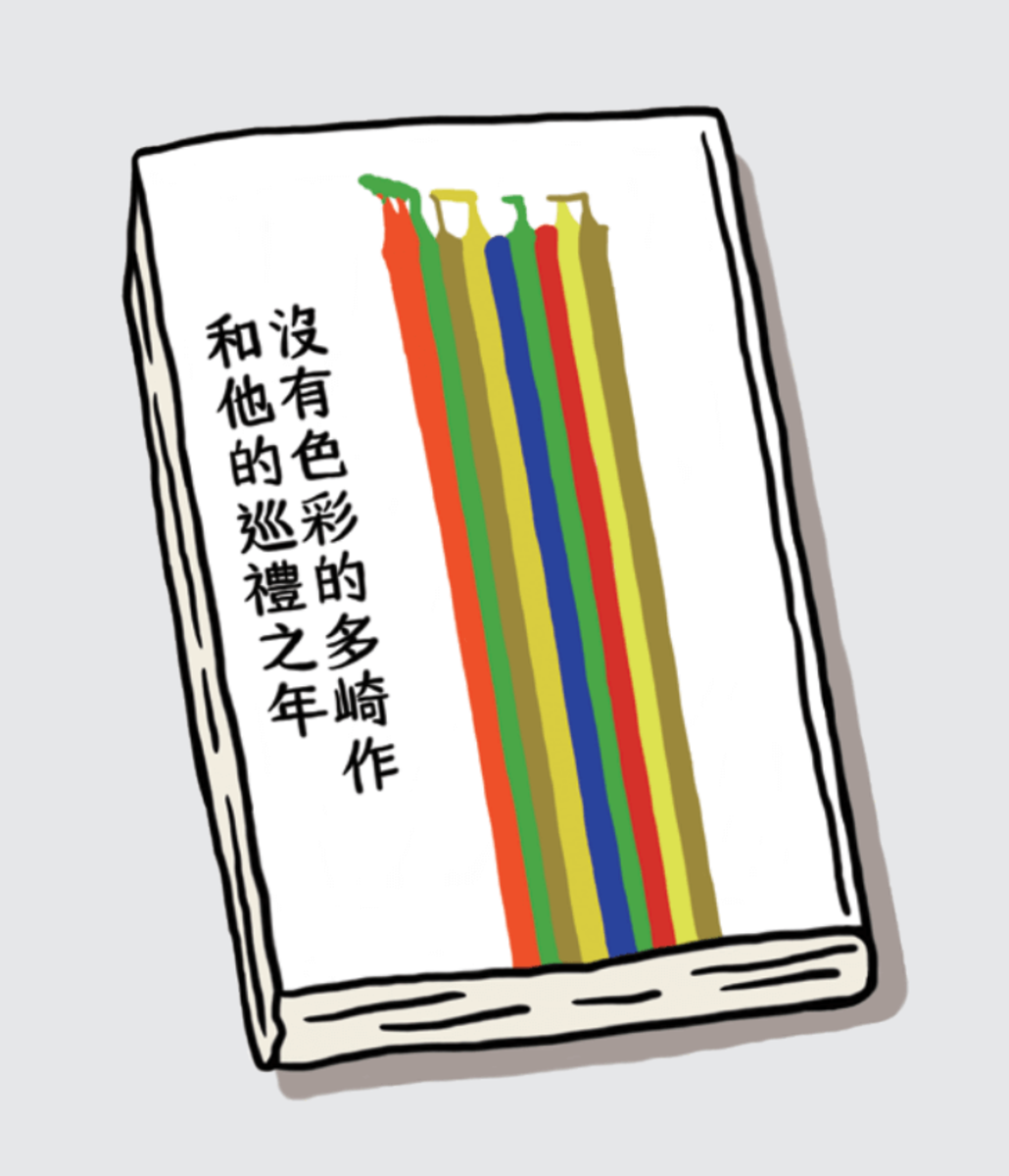Articles
近期文章
Links
相關連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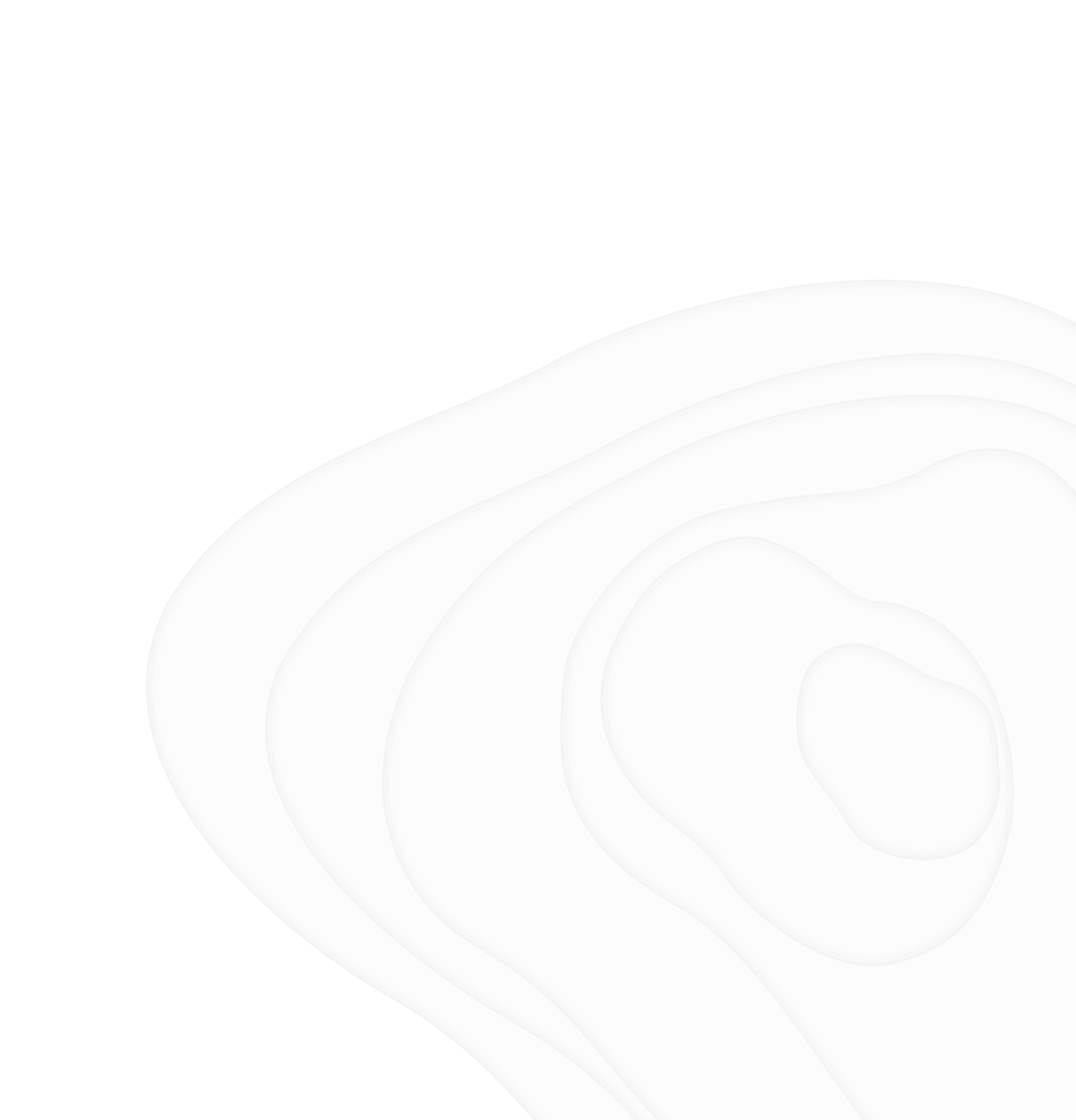
ANIMAL WHISPERER
Tag
Share
專訪寵物溝通師與獸醫師 張婉柔
只要有顆渴望瞭解對方的心, 跨物種對話不是問題
採訪整理 |葛林派
圖|Pinzi Hsu
不少人一聽到「動物溝通」,都會心存懷疑,怎麼可能有聽得懂汪星人和喵星人在說什麼?甚至不用實際看到對方,就能遠端通話?但如果有一位獸醫師也跑去學動物溝通,是否代表這也許不是騙術?
師承國際動物溝通師羅西納(Rosina Maria Arquati)的張婉柔,是台灣首位跨足動物溝通界的獸醫師,她深信人類和動物一樣,都是地球上的住民,雖然長得不一樣,說不同的語言,但只要有一顆渴望瞭解對方的心,跨物種對話不是問題! 動物溝通諮詢生涯即將屆滿九年的她,綜合七年獸醫臨床實務、安寧療護、失落調適、整合療癒等領域的經驗,陪伴過許多的家屬和寵物,一同面對最難過的離別,在他們對彼此說再見之前,把滿滿的愛與眷戀,好好地傳遞到對方心裡
那個年紀的我,還不懂如何面對這樣的失落和調適心情,甚至是釐清生命終結與自我能力的分界。每次失去一隻動物都會很傷心,經常在診間與飼主一起掉眼淚,我很能理解那種無力和難過。以理性的角度來看,動物的死亡是因為生命走到盡頭,但當情感上沒辦法說服自己的時候,我不得不開始思考:這就是我要的嗎?我選擇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出國進修,回國後,進入了老字號、口碑很好的中途團體「流浪動物花園協會」,服務的對象從「寵物」,轉為「等家的動物」。
我的業務是照顧協會內部待送養的動物,有些個性較為緊張、疏遠人,我曉得信任感不是靠藥物就能改善的,身為一名獸醫師,雖心理疼惜卻也愛莫能助,這成為日後我個人想要探索動物溝通的契機。在協會裡,我遇到一隻名叫「祥祥」的小黑貓。祥祥一來就吸引了我的目光,她很兇,不願意讓任何人接近,但我知道那是源自於害怕的表現,激發我想照顧、與疼惜牠的母性本能。
我沒有刻意馴化她,只是以人類的本能和她相處:動作放慢、說話輕柔小聲、情緒穩定等幾個原則進行互動,帶給她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和預期感,將籠子放入娃娃和毛毯並就近照顧。剛開始,她緊張到無法看清楚我拿的食物,手一揮給打翻了;到後來,她會主動來找我玩,還讓背朝向我、要我摸她。這一共花了三週的時間。這是我的一次成功經驗,但三週畢竟也是不低的時間成本,隨著協會積極找中途單位來幫助有類似狀況的動物時,我不禁異想天開:有沒有更快的方式?於是,我走進「動物溝通」的教室。
動物溝通是憑藉著人與生俱來的直覺力,去感同身受動物的情感和想法,平等地把動物視為應該尊重的個體。雖然目前科學界尚無法徹底證實直覺力的機制,但超乎人類感覺四維以上的「信息場」的存在與運作正漸漸被揭露。
要是你問我,動物溝通有沒有改變我實際生活中跟動物的互動?我會說有,但改變的是我自己。我更重視「聽」而不急著去說服,「接受」動物的本質和個性,而不是要牠來配合我的期待;即便「聽」得懂動物的感知,我一樣需要學習和理解動物的肢體語言和物種需求,確保自己的肢體語言跟我的意念有一致性的表達(人的身心不一很容易讓動物產生疑惑),並更加留意去修正我「以人為中心」的想法,期待自己成為心思更為細膩、更體貼動物的好同伴。
何謂「動物溝通」?
經由人的本能⸺也就是所有的感官覺,包括視覺的影像、聽覺的聲音、嗅覺的嗅聞、身體的感受綜合而成的「直覺」⸺以「心電感應」的方式,與動物進行訊息的傳遞和交流。
怎麼看待動物溝通?
飼主與動物生活時,還是要回歸最基礎的「感官覺」。動物無時無刻都在用肢體語言對你表達,如果你沒有學習去「讀懂」,一味地依賴動物溝通師,並不是一個長久的互動方式;你得先好好去瞭解這個物種,對於牠釋放出的訊息有實際的體驗和認知,再來談所謂的動物溝通。 動物溝通的優點在於,動物可以第一時間表述牠們的感知,可以增加飼主對於動物感情面的認識;缺點則是存在「偏誤」的風險,也就是接受動物訊息的溝通師本身是否真的夠客觀,足以準確地理解其中的意涵。 動物溝通師有點像是採訪記者。我們在第一線接觸當事者(動物),把接收到的訊息,經由自己的認知進一步消化、詮釋,寫成一篇報導。不同的記者去採訪同一個人,寫出來的文章也許會有重複的部分,而其他部分則會因為切入的角度和觀點不同,以及個別的生命歷練,形塑出各異的結果。 動物溝通師也像是藝術家,有各自擅長使用的創作媒材,有些人會玩聲音,有些人會玩視覺,有些對空間或顏色特別敏銳,依據個別的感官覺會造就出不同感知力的動物溝通師。
動物溝通在什麼時候派上用場?
當動物的生命走到最終階段時,我可以更細膩地(對飼主)傳達出動物的情感。 對於飼主而言,飼養動物的過程很像在談戀愛,最精華的時段通常是動物最健康、活動力最好的階段;一旦動物開始生病,動物的行動開始限縮,生活逐漸把重心聚焦在「病」,可能因為許多強迫性的護理行為,導致飼主和動物的關係變調;如果動物又在此時過世,飼主最後的記憶便停留在強迫動物吃藥的畫面,或者為了動物健康狀況而不能給予動物如過往 般快樂的自我苛責。 這些都會造成飼主在情感上不同層次的抵觸,有的飼主可以自我調適,有的飼主會陷入沮喪和挫折,難以抽離,這時動物溝通就是很好的切入點,讓飼主有機會可以聽聽動物們怎麼說。 當動物表現出排斥,多數是因為對飼主的行為感到不喜歡,但牠並不是討厭你,更多時候是充滿對飼主的眷戀和關心。我一方面,第一時間直接傳達動物的需求和想法,另一方面再依照獸醫師的專業,包括對於照顧上的理解、環境豐富化的安排和近來學習到的安寧技巧等等,去與飼主溝通可以怎麼調整實務上的作法,讓動物獲得更友善和完善的照護。 其實讓飼主內心感到安穩,也是我在動物溝通工作中,很重要的一個方向,飼主和動物是共生的,是相互影響的。當飼主內心感到不安時,他的情緒與焦慮會很直接地影響到動物身上,對動物本身的狀態一點幫助也沒有。
飼主要如何面對動物即將死去?
當我們把動物視為一個完整的個體,理解到,牠正在經歷生命的必然歷程,盡可能讓牠的身體舒適、情緒安穩自在,讓牠可以和飼主有更好的互動,飼主也能從動物那獲得回饋和支持,在生命的最後創造一個很好的循環;即便之後要走向永遠的離別,至少最後留下的回憶是甜多於苦。在彼此陪伴的過程中,付出什麼?看見了什麼?改變了什麼?留下了什麼?才是一段關係的精髓。傷痛一定會有,但在難過的底下,還有很深刻的影響和意義等待我們去發掘。
讀一讀 作家筆下的友誼
文| WenLin 插畫| Pinzi Hsu
1
0
1
2
3
4
5
6
7
8
9
0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