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滑看更多內容
Articles
近期文章
Links
相關連結


TIME ZONE
Tag
Share
把日常作息視為創作的一部分
文|Fion Chang
圖|楓楓
幾點起床、幾點吃飯、幾點上學⋯⋯我們的日常生活貌似被待辦事項推著走,很多身不由己之外,也有許多被告知的「應該」。但是真的是這樣嗎?如何過每一天,是選擇,也是最實際的一種創作。就像每個時代都有截然不同、超乎想像的創作,那些創作者的日常同樣沒有公式,只有他們忠於自我的取捨——因為他們有更高的目標,很自然地產生了生活的優先順序。從他們的日常,我們可以看到:當你有了清楚的目的,作息會成為一種主動積極的選擇,無論是怎樣時間安排都有其道理存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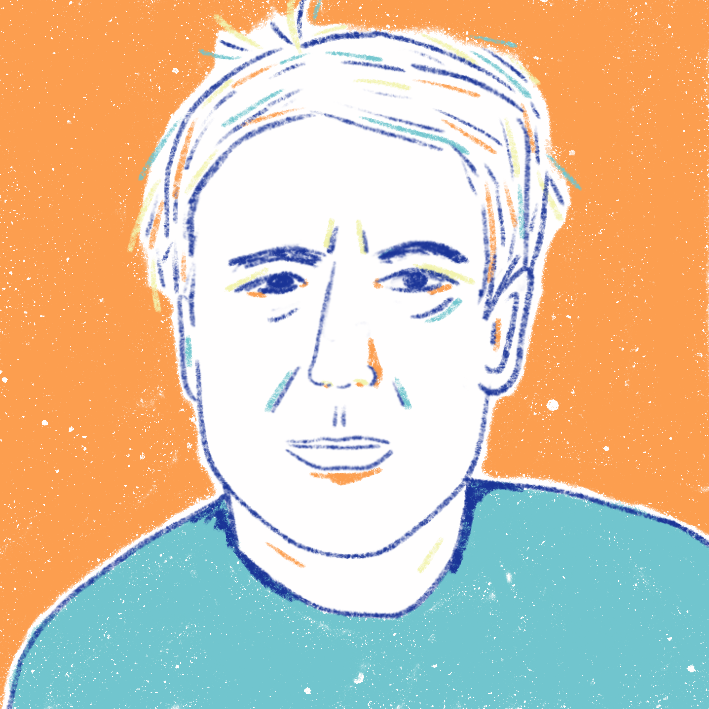
風格是一種催眠般的重複
關於春上村樹生活方式的書寫,幾乎和他的作品一樣多,也一樣充滿魅力。他曾在訪談中提到,「寫長篇小說時,基本上都是凌晨4點左右起床,從來不用鬧鐘。泡咖啡、吃點心後,立即開始工作。」寫作數小時後,他會去慢跑一小時,在這段只有自己的時間中很自然地跟隨身體的節奏與內心展開對話。午睡30分鐘,醒來馬上再次投入工作。他不太社交,旅行也不拍照,大量閱讀、享受音樂。日復一日,他意志堅定地過著像是僧侶一般自律的生活,有人稱呼他為「生活家」,但他只是很清楚自己適合怎樣的生活。選擇不隨波逐流,他將每一種喜歡進行到底,於是成就了一種強烈的風格。
早晨的一杯入魂
貝多芬的作息也是規律地出名:每天晚上10點休息,早晨6點起床,簡單的早餐之後就開始作曲8小時,即使出外散步也會隨身攜帶鉛筆和五線譜。在開始工作之前他有一項重要的儀式:為自己煮一杯咖啡,一顆一顆仔細數算60顆咖啡豆慢慢煮。這並不是什麼神仙配方,貝多芬說過,「咖啡的味道並不重要,重要的是內心的平靜。」貝多芬的作息乍看之下沒有村上春樹那麼嚴苛,卻也十分純粹,並且重視心靈的平靜。他的作品以情感豐富、技巧精湛且勇於創新見長,也許早晨的第一杯咖啡就像一條神祕的隧道,帶領他放下不必要的瑣事,直抵創作的心流。


人間詞話夜來香
寫出《望春風》等多首經典臺語歌謠的李臨秋,事實上是白天與夜晚都很精彩的全時段生活者。白天的他有精實的職業,從會計、總務到創業,李臨秋一直都是認真的上班族,顧好家裡的生計。「深夜、燒酒、夜來香」,下班之後的李臨秋在夜深人靜後慢慢沉澱白天的見聞,加上溫熱的紅露酒催化靈感,透過夜來香花香將思緒連結回那些市井小民的日常故事中。他也會在酒家和文友相聚,看盡人間情愛,有時候則會邀請他們來家裡一起談談唱唱,而那些通俗卻意境深遠的作品,都是這些酒酣耳熱的夜裡的雋永回憶。
生活是次於作品的存在
當標準晨型人們的一天都過完大半了,普魯斯特的一天才正要開始。下午3、4點,甚至是晚上6點,都是他的起床時間,「早餐」不是食物,而是用來緩解哮喘的鴉片,有時候一抽就是幾小時,然後才是咖啡與麵包。普魯斯特會在晚上打電話、梳妝打扮、和朋友交談數小時,把這些聊天中的弦外之音與情感流動當作寫作的素材。有些時候也可能是躺在床上寫作,就著微弱的燈光弓著身子工作。「一位作家作品的深度,取決於穿透作家心靈痛苦的深度。」在普魯斯特不太「正常」的作息中,卻也孕育出了非凡的故事。

1
0
1
2
3
4
5
6
7
8
9
0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1
2
3
4
5
6
7
8
9
0



